 “愤怒的对立面不是冷静。这是同理心。
“愤怒的对立面不是冷静。这是同理心。
去年12月,我去印度学习瑜伽和冥想。在我训练大约一周后,我注意到我变得越来越生气。
我以为来到这个宁静而支持的地方,在完善我的瑜伽练习的同时,一切都是为了温和的治疗。相反,我很生气,非常消极,对一切都感到沮丧。
最终,我和我的老师交谈,并分享了我自从开始担心以来所经历的事情。他們解釋說,由於訓練很強烈,而且我們正在做很多活動來淨化身心,任何被困在內在的能量都想要釋放。这种清洁过程可能表现为不必要的消极情绪、疲劳、情绪失衡等等。
虽然这让我感到安慰,但我不知道如何处理这种愤怒,如何处理它。于是我问自己:“生气的时候我在想什么?
答案很简单——其他人。
自从我把自己从我所认识和熟悉的一切和每个人中抽离出来后,我周围有一种寂静的感觉。这让我的愤怒变得非常响亮。
我最初的想法是所有不支持我去印度决定的人,至少一开始不是。我重播了人们试图改变主意或告诉我应该做其他事情的所有场景。
几天后,旧的情况开始出现。六个月前发生的事情,当有人说了一些伤害我的话时,我保持沉默。或者当人们告诉我我不能做某事时,我相信他们。
在经历了两个星期的内心愤怒之后,我以为我的头快要爆炸了,然后有一天,感觉好像爆炸了。我醒来时发烧严重,鼻窦感染,脸部受伤。我整天哭泣,甚至不能上课。最终,我住进了急诊室。
我记得遇到过一位有着橙色头发和温柔微笑的阿育吠陀医生。他给了我一些阿育吠陀药物,并说我会在四天内感觉到100%。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我觉得太虚弱了,精神上被打败了,无法抗议,所以我吃了药。
头两天我躺在床上发高烧,几乎没有力气动弹。第三天,发烧消失了,我可以吃东西了。第四天,我感到精力充沛,准备继续学习。
最令人惊奇的感觉是我健康后感到的轻盈。我的愤怒从根本上减少了,我更有耐心,更快乐了。
这种平安和喜乐的状态促使我审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首先,我知道我的疾病是由于积累的负能量在寻找出路而显现出来的。坦率地说,我很感激我能够发布它。
然而,愤怒仍然主宰着我的日子。起初,我开始审视所有我认为以任何方式冤枉我的人。我试图原谅他们并合理化他们的行为,同时培养每个人从他们的感知水平行事的理解。虽然我可以缓解愤怒的感觉,但它仍然在我的生活中非常存在,我每天都能感受到它。
然后有一天,当我坐着冥想时,一个深刻的领悟浮现在脑海中。我无法放下愤怒,因为我不是在生别人的气,而是在生我自己。
由于我允许我不喜欢的事情,并且从不说出来,在内心深处,我知道我背叛了自己。然而,我对认可和包容的需求比我为自己挺身而出的愿望更强烈。
由于承担促成这种行为的责任是面对的,我把愤怒转向他人并责怪他们。
虽然这种认识很不舒服,但它给了我一种力量感。意识到我的力量在于自我负责,这让我感到自己被赋予了力量。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与自己作斗争,有时感觉自己像个受害者,同时又重新专注于我的新顿悟。
以下是我决定继续前进并开始放下我的愤怒的方式,一旦这种情绪动荡稍微稳定下来,我可以清楚地思考。
1. 我专注于我的力量在哪里。
由于我习惯于感觉自己是受害者,因此对我所容忍的事情负责是新的、陌生的和不舒服的。因此,我经常陷入受害者的境地。
一旦我观察到它,我就重新集中注意力,并提醒自己从一个负责任的地方生活是多么令人惊奇和自由。最终,我觉得自己不像一个受害者,而更像是一个可以做出选择的健康个体。
我们回避对自己的思想和情绪负责的最常见原因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意味着让人们摆脱困境。我们希望他们意识到他们是如何冤枉我们的。我们希望他们能验证我们的感受,我们相信,如果我们保持愤怒的时间足够长,它就会发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是受苦的人。责任一词源自“响应”一词。而这一点,我们可以选择。同样,我们可以选择设定界限,同时定义我们容忍什么并对自己负责。
经过几个星期的心理乒乓球,我知道我缺少一个组成部分。
2.我决定原谅自己。
没有宽恕,我不可能经历这个过程,因为我对自己所允许的事情进行了深刻的评判。
自我宽恕是最艰难的一步。虽然我过去练习过自我宽恕,并且非常熟悉它,但原谅自己破坏了我的心理和情绪健康是一颗难以下咽的药丸。
每次我闭上眼睛,开始说出我的宽恕肯定,我就开始哭泣。我意识到我不相信我应该得到宽恕——这种信念源于我创伤性的童年——所以我决定将内在儿童工作纳入这种实践中。
我创造了一个成年和年轻时在长凳上相遇的愿景。每次我们见面,我都会请她原谅我让她失望,伤害她那么多。
经过一个星期的有意识的练习,我的心开始软化,我可以用更多的同情心和同理心来看待自己,而不是严厉的批评。
这在我的治疗中产生了巨大的转变,因为我在治愈我们生活中的任何事情时都意识到了一个基本真理。为了放下愤怒、内疚、羞耻、评判或我们喂养的任何其他消极情绪,我们必须走到光谱的另一边,拥抱关怀、养育、理解和同理心的情绪。
内在小孩的工作、练习自我宽恕或慈爱的冥想只是我们能做的一小部分,以缓解我们的康复。
当我准备回国时,我知道我还有一件事必须落实到位,才能使这个过程持久和成功。
3. 我选择了我的不可协商的。
是时候划清界限,决定我今后能容忍什么了。我记得当时我感到非常害怕和不确定。让我害怕的不是边界本身,而是那些不习惯边界的人的反应。
起初,我觉得自己像个蹒跚学步的孩子,迈出了第一步。我来来回回,思考我的界限是好是坏,是对还是错,以及我是否真的需要把它放在适当的位置。然后我意识到了一件事——当涉及到我们的界限时,没有对错之分。我们设置它们,仅此而已。它们是我们的不容谈判的,它们不容辩论。
当我们开始设定界限的那一刻,我们就会尊重自己。我们正在向我们的大脑发送一个信息,说:“我爱自己,重视自己,尊重感觉正确的事情,放下不对的事情。我们也准备在坚实的基础上建立关系。
重要的是要承认设定界限带来的恐惧。我们害怕失去人吗?我们是否担心自己不会被验证,或者其他人会对我们感到不安?
尽管这些担忧是有道理的,而且我们都在与它们作斗争,但重要的是要提醒自己自我破坏和自我背叛的代价。这种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续或不健康的,最终,它会让我们重新面临同样的挑战。
几个月来,我一直在改变我的人际关系以及我如何驾驭它们。尽管其中一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我能够克服愤怒并放下生活中的许多消极情绪。
我仍然陷入我的受害者身份,并试图让自己摆脱困境。然而,我现在更善于识别它,同时理解我对自己的生活负责的特权,以及当我采取行动时它的感觉是多么强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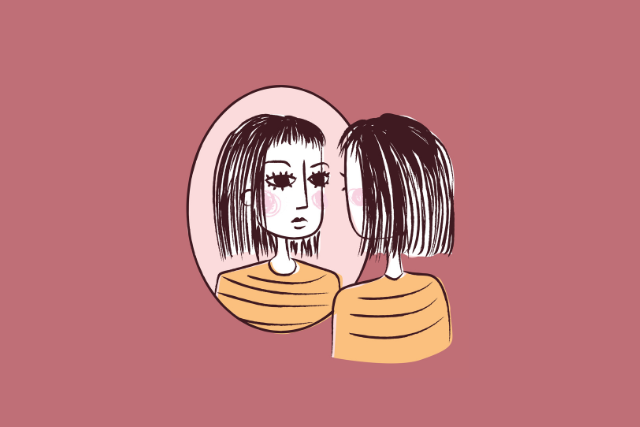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