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不是通过找到一个完美的人来爱,而是通过学会完美地看待一个不完美的人。”
“我们不是通过找到一个完美的人来爱,而是通过学会完美地看待一个不完美的人。”
像我们许多人一样,我一生中与母亲的关系最好用复杂来形容。
在我们的旅程中,我们经历了相当多的动荡时期,她在我成长过程中的酗酒和吸毒在各个层面上都助长了巨大的功能障碍:我十几岁的时候(是的,杰里·斯普林格式的)字面上的身体冲突,看似持续的叛逆行为,完全缺乏理解,深深的不信任,不愿意(甚至可能当时无法)改变, 最终在我十三岁时完全分离,这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改变。
今天,我已经四十八岁了,我和母亲已经重建了二十多年的关系。
我深深地认识到,她在2001年决定保持清醒,这为我培养了尝试建立关系的意愿奠定了基础。要走到今天,我需要做很多非常个人化的内部工作,我希望通过分享我的故事,你可以在旅途中感受到希望甚至灵感。
我出生时,母亲才二十岁,两年后姐姐出生时,我的父母已经离婚了。我的母亲在十四个寄养家庭中长大,十八岁时决定离开这个系统,不寻求与家人的联系,成为我们家中第一个打破周期的人。(我现在很清楚,她是多么没有能力为人父母。
我和姐姐和母亲住在一起,我们周末去看望父亲,但从来没有一个一致的时间表,因为一致性不是一个可以描述我们童年任何部分的词。五岁时,我和父亲短暂地住了一年,姐姐和妈妈住在一起。
由于与父亲的不一致联系,多年来我理想化了他和他的生活,这经常成为我母亲争论的焦点。
到十三岁时,我已经厌倦了与母亲的生活,每天都幻想着创造一个新的生活。在一次特别可怕的经历之后,她喝醉了来到我的学校,拽着我的头发把我拖出学校舞会,我决定采取行动,为我和我的妹妹寻求庇护,与八个小时车程外的父亲住在一起(我的祖母帮助促进了这一点)。
当我们离开母亲的家时,我们已经有几年没有和她联系了。她搬离了加利福尼亚,我把注意力转向了和父亲一起过上令人兴奋的新生活。男孩,我是不是比我想要的更惊喜和更兴奋!
1989 年,当我们和他一起搬到南加州时,我父亲在蓬勃发展的科技行业工作。他在一个时髦的新开发项目中为我们建造了一栋房子,起初,真的感觉生活正在变得更好。
直到它不是。真的,真的不是。
有一天,我父亲出去理发,三天没有回来,把我们留给继母,她从来不想要孩子,也不想让我们来和他们一起生活。当他回来时,他衣衫褴褛,没有理发,而且非常安静。
通过继母在我耳边低语的愤怒咬牙切齿,我发现我的父亲是一个几乎无法运作的吸毒者,他喜欢可卡因、海洛因,并最终死于他的死亡,快克可卡因(快克绝对是打击)。
正如我祖母所说,我们从煎锅里跳进了火里,在和他生活了不到两年之后,他在我十五岁的时候自杀了。由于我们和母亲没有关系,也不想要关系,我的祖母亲切地收留了我们,我再次将注意力转向开始新的生活。
在我十六岁的时候,我决定我的父母都是失败者,我只想和祖母一起继续我的新生活。我把注意力转向了学校,但为休闲饮酒、尝试 LSD 和蘑菇以及去湾区的金属音乐会腾出了足够的空间。
我十八岁就上了大学(考虑到我的直系亲属中,我的 GPA 还不错),我决心成为下一个打破周期的人,因为我比我来自的地方做得更好。
直到看起来我不会变得更好或做得更好。
我二十岁的时候意外怀上了儿子(就像我妈妈一样),在大学期间,这个消息并没有得到我祖母的好评,她“以为我会与众不同”。我仍然决心打破这个循环,而我祖母的评论将助长多年来为了证明自己的努力而取得的超额成就(我令人难以置信的倦怠故事是另一天!
我试探性地向我母亲伸出了橄榄枝,允许她在我儿子出生时来医院,只要她清醒(以及其他规则)。又过了四年,我生了第二个孩子,她又要经历一次致命的酒后驾车,才能选择清醒。对我来说,这是深度治愈和转变的脆弱开始,需要很多很多年。
“作为受过创伤的孩子,我们总是梦想着有人会来拯救我们。我们做梦也没想到,事实上,作为成年人,它会成为我们自己。 ~爱丽丝·利特尔
我可以分享我做过(和做过)的四件事,这些事情帮助我来到了我能够与母亲建立积极关系的地方,毕竟在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关系都出现了功能障碍。
1. 我看着我母亲小时候的照片,并把它们记在心里。
小时候看到我的母亲帮助我把她看作不仅仅是我的母亲。我看着我母亲年轻时的照片,想象着她小时候经历的创伤,以及那个小女孩忍受了多少痛苦和折磨,影响了她如何成长为成年人和父母。
这种做法给了我洞察力,并帮助我对她和她的旅程产生了同情心。
我了解到我有能力有意识地选择另一种视角,另一种看待她的方式。想象她小时候的样子,想想她多年来慢慢与我分享的经历,给了我新的光和新的眼睛来看待她。
当我需要培养对她的同情心时,我仍然会使用这种做法,因为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并不在同一个地方,有时我在与她互动时需要这种提醒。
2. 我有意识地决定放弃我关于我希望她成为的母亲的故事以及我童年时期的受害者心态。
首先,我必须深刻地意识到我告诉自己关于我母亲和童年的故事。在我的日记中写下它对我帮助最大,因为我知道这是我的私人和神圣的地方,如果我不想与任何人分享,我不必与任何人分享。
我问并回答了诸如“谁是我的母亲?我对母亲有什么感觉?我希望我的母亲成为谁?我怎么希望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有所不同?我童年最美好的时光是什么?最糟糕的部分是什么?
一旦我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感受和对自己经历的看法,我就有意识地决定放弃我希望我拥有的母亲的故事,以及我感觉自己在家长部门受到了可怕的对待。我有意识地决定,我不是童年的受害者,也不是母亲的受害者。我接受并最终接受了我所有的经历帮助我成为今天的我。
在我的精神和治疗之旅中,我发现有些人相信我们实际上在灵魂化身到今生之前就选择了我们的父母,并且我们选择了一生中能教给我们最多的父母。
这个想法帮助我以不同的方式看待我的母亲和我的童年。我现在深深地知道,她是我的完美父母,因为我从来不喜欢被告知该做什么,而且她绝对是最擅长教我我不想要的东西,这样我就可以开辟自己的道路(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她总是说“我是一个警告,而不是一个榜样!
3. 我放下了我作为母亲对她的期望。
社会、家庭、媒体和电影都在为我们描绘父母和家庭应该和不应该是什么。我们既微妙又公开地对自己和他人应该如何行事有一定的期望,尤其是在特定的角色中,比如父母的角色。
通过深入观察,我意识到我对我的父母应该是什么样子有很多期望,这些期望是不现实的,甚至不公平,因为他们实际上是谁。认识到我的期望并有意识地决定让他们离开,这让我为我的母亲创造了空间,让她成为她自己,而不会在她不能成为或做我想让她做的事情时感到失望。
4. 我为自己的关系创造了界限,从对我们俩的爱和同情的地方。
我深入研究了我作为一个有意识的成年人需要什么才能与母亲建立积极的关系,我创造了界限来支持自己。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这些界限来自对我们俩的爱和同情,目的是保持我们的关系积极。
真正帮助我建立关系的一个界限是注意我们谈论的内容以及我选择如何回应。
例如,我们通常不会对政治有相同的看法,所以我设定了界限,我们只是不谈论这个。如果她碰巧说了一些我不同意的政治言论,我通常什么都不说,因为死在那座山上对我来说真的没那么重要(我试图找到一种善意的方式来转移话题而不参与)。
我母亲的感受不同,但我相信她仍然需要对她小时候经历的创伤进行深刻的治疗。这个话题已经成为我的一个界限,因为我们还没有到可以就此进行深入对话的地方,这没关系。我已经接受了我们现在不能去那里(也许永远不会去那里),所以我选择放手。
这也极大地帮助了我记住,我们都在以我们目前的意识水平尽我们所能,无论我们在旅程的哪个阶段,总有更多的东西需要学习。这个提醒帮助我培养对母亲(和其他人)的耐心和恩典。
虽然我不会把我们的关系归类为完美的,但我开始了解到,没有完美的关系,但有时努力拥有一段不完美的关系是治愈的完美良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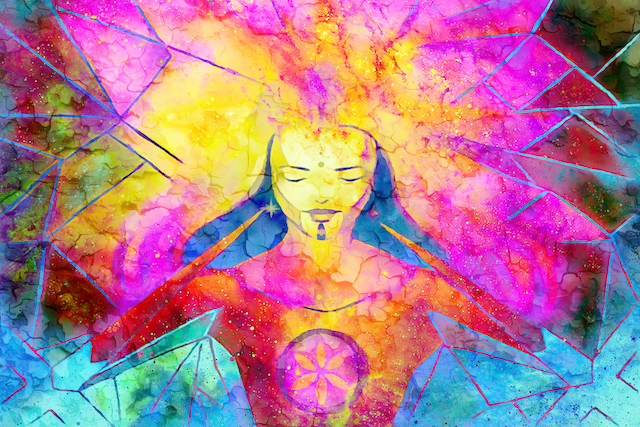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